|
南宋与元代,秀州港口群是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出发港和目的港。港口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北岸和吴淞江下游。杭州湾北岸的港口主要是澉浦与乍浦,吴淞江沿岸的港口是主要为青龙镇与上海镇。
秀州在内河航运、贸易市场、丝绸生产三个方面较其他港口有明显优势。内河航运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江南运河与境内运河水网,港口具有海河联运和江河联运的特点。市场方面的优势在于周边是奢侈品消费最集中的区域,对海外的香料、珠宝异珍、贵重木材有大量的需求。秀州又是丝绸重要产地。
今嘉兴的母体——秀州的综合优势,形成了它在宋元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而独特的地位。
历史上的秀州
海上丝绸之路,在宋元时期达到鼎盛,成为东西方文化经济交流的重要载体。现在研究宋元丝绸之路的专家往往认为宋元时期中国丝绸之路的主港是泉州、广州、宁波三个城市,其他港口只是支线港补给港。
这一论点大体上不错,只是遗漏了一个重要的地区,这就是秀州。
在宋元时期,特别是南宋与元代,秀州港口群是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出发港和目的港,对秀州在宋元时代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我们应该给予足够的认识并进行深入研究。
秀州,五代吴越国于后晋天福五年(940)割苏州地建立,管辖嘉兴、华亭、海盐、崇德四县,州治设于嘉兴,其地域相当于今天嘉兴市(不包括海宁)和上海市吴淞江以南地区。进入元代,改秀州为嘉兴路,路城仍在嘉兴,管辖范围仍为嘉兴、华亭、海盐、崇德四县。
华亭县在至元十四年(1277)升为松江府,但仍为嘉兴路管辖,至元二十八年(1291),分华亭县东北地设上海县。这样,元代嘉兴路管辖嘉兴、华亭、海盐、崇德、上海五县,但管辖的地区与五代、宋代的秀州范围相一致,因此本文“秀州”这一概念的范畴也包括元代的嘉兴路。
秀州位于太湖东南,左苏右杭,东对东海与长江口,南临杭州湾,大运河自北向西南贯穿州境,吴淞江从太湖流出,沿着州境北部由西向东汇入长江口。秀
州境内平原沃野,以大运河为骨干的水网体系密如蛛网,只是在杭州湾畔的乍浦、澉浦、黄湾一线分布着不多的山丘。秀州的自然地理环境为它成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宋元时期秀州的主要港口·澉浦
宋元时期,秀州境内外贸港口主要分布在州南部的杭州湾北岸和州东北部的吴淞江沿岸。
澉浦,唐开元五年(717)苏州刺使张廷珪奏置,会昌四年(844)置镇遏使,到南宋时期成为秀州最主要的对外贸易港口。
《澉水新志》说澉浦:“迨南渡后,以澉地近京师,商舶聚集甲于诸方,镇极繁盛。”可见澉浦在南宋时才成为重要的港口,其原因,明代海盐人胡震亨在《海盐县图经》中有精到的解释。胡震亨说:“今考海盐市舶之设,惟宋南渡后最盛,缘宋都临安,系万货所凑,澉浦近畿地,海舶由龛赭入钱塘阻于江湍,以收舶澉堧为便,香货因而聚集。”
南宋建都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经过一百多年的经营,杭州成为南宋政治经济的中心,也是当时世界上最繁盛的大都市和消费的大市场,国内外货物都汇聚于杭州。杭州虽然位于钱塘江口,临近杭州湾,但是却缺少建设成为港口的基本条件,其原因主要是海潮的影响和钱塘江河口的水道受制于龛山、赭山,变化无常。
这就为离杭州不远的澉浦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澉浦位于杭州湾海滨,距离杭州不过百里,当时也就一天的路程,又有内河水路连通杭州,是杭州最理想的海上货物集散替代港,澉浦因此当时被称为“小杭州”。
澉浦自身的港口条件算不上优越,镇东南海边是长樯山和葫芦山,两山基本上沿海平行,没有形成最适合建设港口的海湾。澉浦在长樯山和葫芦山之间开挖了一条人工的运塘通往澉浦镇,运塘的海口设招宝闸,海上船舶到了澉浦,先停泊在长樯山龙眼潭下,由招宝闸入运河进入澉浦市中的塘湾码头,因此澉浦港是半天然半人工的海港。
运塘的水源来自澉浦镇西的山地,山上的水源汇聚于山下,又在澉浦镇西六里设堰阻挡山水流入下塘,形成永安湖,就是今天的南北湖,湖水向东通运塘,一直到塘口的招宝闸,因此运塘的水位是基本稳定的,从而减小了潮汐变化和海上风浪对船只的影响,为海船停泊塘湾码头进行交易和搬运提供了优良的条件。
澉浦巧妙合理利用自然环境条件建设港口,充分体现了规划者的大智慧,是中国古代港口建设的奇葩。
南宋常棠《澉水志》说:“市泊场,在镇东海岸,淳祐六年(1246)创市泊官,十年(1250)置场。”
澉浦在南宋正式设立市泊场,管理澉浦海上贸易事务,其地址位于澉浦东海岸的舷风亭。《澉水新志》引用《海盐县图经》的有关内容叙述了南宋时期澉浦的海上贸易情况,“凡大食、吉逻、阇安、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诸香并通贸易,以金银鍲钱,杂色帛、瓷器市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翡、镔铁、瑇瑁、玛瑙、车渠、水晶、番布、乌樠、苏木等物。香船至,聚长樯山龙眼潭下,由招宝闸入运河。穿镇,西出栅桥,发引收税,抵六里堰搬度下河,流通内郡。其税十分抽一,犀角象齿十分抽二。”
澉浦出口的商品主要是“杂色帛”,也就是各种丝绸以及瓷器,进口的商品主要是香料、珠宝和名贵的木材。交易的地区是东南亚的越南、马来西亚、印尼一直到伊朗和阿拉伯。
南宋《澉水志》说澉浦“东达泉潮,西通交广,南对会稽、北接江阴许浦、中有苏州洋,远彻化外”,而且“人烟极盛、专通番舶”。而澉浦人“不事田产,惟招接海南诸货贩运浙西诸邦,网罗海中诸物以养生”。
《澉水新志》称:“澉浦黄道关税务,宋元最盛。”可见宋代澉浦的海上交易的繁盛。海上贸易的兴盛也推动澉浦镇的繁盛,《澉水志》记载澉浦在南宋初的绍兴年间还是“人民稀少”,而到南宋后期已经是“烟火阜繁,生齿日众”,宋绍定年撰写的《德政碑》中说澉浦镇的规模“不啻汉一大县”。
澉浦在元代继续为中国与东南亚、西亚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这与杨氏家族有密切的关系。杨发,南宋时曾经任殿前司选锋军统制官、枢密院副都统。元兵南下,杨发降元,被任“明威将军,福建安抚使、领浙东西市舶总司事”。杨发家住澉浦,经营海运,“至元十四年(1277)立澉浦市舶司,令安抚使杨发督之,时设庆元、上海及澉浦三市舶司,并发领其事。”三市舶司中,澉浦与上海市舶司都在嘉兴路管辖范围内。
杨发除了管理庆元、上海及澉浦三市舶司外,“每岁招集舶商於番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次年回帆。其税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取一,然后听其货卖。”由市舶官直接招集商船到东南亚与西亚进行贸易,开创了海上贸易的新形式。
杨发有自己的船队,也参与海上贸易,这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形式肯定不符合市场规则,但其直接的效果是造就了杨氏家族的巨富。《海盐县图经》说:“总领舶务杨发者,土著澉川,其家复筑室招商,世揽利权,富至童奴千指尽善音乐,饭僧、写藏、建刹遍两浙三吴间。”
杨发的儿子杨梓与孙子杨枢继承杨发的事业,从事航海贸易。杨梓官至杭州路总管、海道都漕运万户,在澉浦“以己资广构屋宇,招集海商,番舶皆萃于浦”。杨枢于大德五年(1301)、大德八年(1304)出使西洋,并进行海上贸易,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航海家。
除了杨氏以外,澉浦还有许多从事海上贸易的家族,元代嘉兴著名画家吴镇的祖父吴泽就在澉浦经商,并有自己的船队。《义门吴氏谱》记载,吴镇的父亲吴禾“家巨富,人号大船吴”。
澉浦在元代港口地位相比于南宋,其实呈逐步下降趋势。其主要原因是,元代的杭州虽然还是东南一大都会,但相较于南宋的临安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临安是南宋的都城,皇室、官僚、巨富豪商云集,商贸繁盛,是全国的商业中心。元代的杭州只是区域和地方的商贸中心。杭州商贸地位的下降当然影响主要为其服务的港口澉浦。
元代支撑澉浦海运还能维持兴盛局面主要因素有两条,第一是前面提到的澉浦杨氏的因素;第二是元代海上漕运,澉浦是元代海上漕运的主要港口。到了元后期,杨氏衰落,漕运规模减小,澉浦的海上商贸活动大受影响,“大德二年,始并澉浦入庆元提举司”,是澉浦海上贸易地位下降的必然结果。
宋元时期秀州的主要港口·乍浦
在澉浦地位下降的同时,澉浦东面杭州湾畔的乍浦却兴盛起来。
关于乍浦,《乍浦志》卷一《新开水门记》中写道:“乍悬海上,为浙西形胜,大海以南则为岛衣披法不毛之地也。宋元时并村落、通互市,以是招隙。”
《乍浦志》又说:“乍浦故海盐东偏,自钱氏王吴越,置镇遏使,宋季设水军统制,名稍稍著。元通海道,番舶骈集。”说明乍浦虽然成镇于五代,宋代已经“通互市”,但成为重要对外贸易的海港却是在元代。
乍浦在港口条件方面非常优越,它地处杭州湾中部,海面广阔,不受钱塘江潮的影响,背靠九龙山,有优良的港湾,离海湾不远有几座海岛,形成天然的防波屏障,是杭州湾中最好的天然良港。
乍浦在南宋主要是军事港口,是拱卫京师的军事重镇,到了元代才成为贸易港口。元代乍浦能取代澉浦成为杭州湾的主要外贸港口的原因,大致分析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南宋临安商贸兴盛时,澉浦有距离临安路途近的优势,随着元代杭州商贸地位的下降,澉浦的重要性也随之降低;
元代海外贸易规模较宋代更为扩大,对外贸易主要依赖海路交通,元代京杭大运河开通,澉浦与乍浦港都与嘉兴运河水网连接,通过运河与全国内河水运网络有机联系,这一优势使得杭州湾北岸嘉兴的港口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目的港,广东、福建的港口的货物大多还需中转到这些港口再输往内地,港口业务的扩展对港口条件的要求有了新的要求,澉浦作为半自然半人工的港口,港口逼仄的劣势就显现出来,已经不适应海上贸易的需求,而乍浦港口条件的优势就得到充分的显现;
元代疆土幅员广阔,是世界第一强国,在军事上没有势均力敌的对手,乍浦所以能由军港转型为商港。综合这几方面的因素,乍浦最终取代澉浦成为杭州湾北部最重要的港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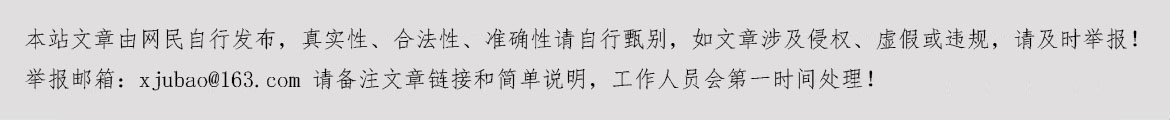
| 








